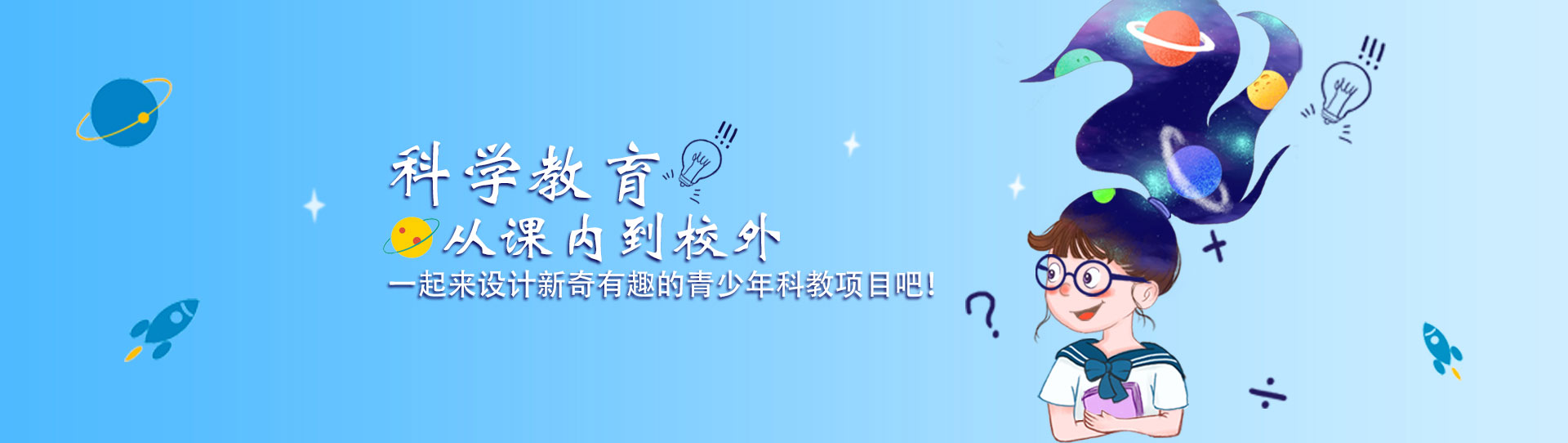kk体育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全面部署,教育事业被提升到了新的发展高度,但是,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的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始终难以确定。教育培训机构的问题也成为2018年各大报纸讨论的热点,《中国教育报》发文确定河北将建校外培训机构问题台账,《中国人口报》为过热的校外培训“降降温”,《安徽日报》质问校外培训如何告别“野蛮生长”。这就说明,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亟待明确,只有确定了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才能使教育培训机构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教育培训业将会进入更加繁荣的发展时期,教育培训合同也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学习生活中,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对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规制。教育培训合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不是围绕教育培训机构而产生的。目前教育培训机构与接受培训一方的关系紧张kk体育,多因教育培训机构的身份问题引发,在司法裁判时,法官往往因教育培训机构的地位问题而举棋不定,严重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可操作性。因此教育培训机构地位的确定将有助于司法裁判的顺利进行和教育培训业和谐秩序的构建。
教育培训机构在国民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kk体育。就教育培训机构来说,法律地位得以确定不仅有利于立法机构对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而且会更好地为执法和司法裁判提供理论基点。总而言之,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得以确定将会结束教育培训机构混沌的现状,真正实现教育培训机构由“野蛮生长”转向“有序发展”。
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确定为商主体之后,为执法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不再使对违法教育培训机构的清理整顿无法可依。在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监管执法时,由于教育培训机构和接受培训一方信息不对称,必须充分进行利益衡量,无论是法律责任的担负还是执法的目标追求都应该把受培训者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培训机构、教师及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处于次要考量地位。在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之场合,优先考虑民事责任,并主要采取停止侵害、民事赔偿、继续履行等补救方法。在出现教育培训机构违法情形后,救济可结合如下因素考量:是否有补救的可能(是否继续履行)、可得利益损失及违约金、人格权侵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解除合同。在各因素的考量基础上,对教育培训机构和接受培训一方进行利益衡量,进而得出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今年,教育部的一系列改革制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全面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举措就剑指教育培训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多次被社会关注多因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界定、法律地位等问题始终得不到法律的回应。 随着社会关注度的日益提高,对教育培训机构法律地位的相关研究俨然成为民商法领域的前沿性课题。如何准确界定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并确定其法律地位是今后教育培训业法律规制的前提,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使教育培训机构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界定过程,也是判定教育培训机构法律特征的过程,教育培训机构有着不同于民事主体的特殊性。首先,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立需要严格遵循《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获得均需要国家的程序授权,未满足《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准入条件,均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所指之教育培训机构。其次,教育培训机构的本旨是其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教育培训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营利,并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提高教育培训水平。最后,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教育培训关系中的当事人,积极地参与教育培训活动,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义务。
《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该条文是我国《教育法》关于教育培训机构的规定,这基于中国教育的现实环境及政策,否定了教育培训机构的营利性,此规定也使教育培训机构的存在于法无据,也是教育培训业频发监管乱象的缘由之一。2017年开始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规定: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就《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说明教育培训机构的存在被法律所容许,不再采用《教育法》中全盘否定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的做法。通过对《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比较可知,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我国的教育政策也有了变化,不再保守地将教育统一于公益性,而是遵循市场规律,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模式讨论,这也就给教育培训机构的研究提供了前置性依据。
【摘 要】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整个国民教育生活中迅速崛起,因教育培训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由此各种监管措施接踵而至.但是,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始终模糊不清.本文结合教育培训机构的研究现状,界定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进而明确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多角度对明确教育培训机构地位的现实意义进行阐释,意在破解教育培训机构法律监管之疑惑.
[1] 胡东成,彭瑞霞. 我国教育培训机构标准建设的研究[J]. 继续教育,2011(7):6-10.
[2] 曾晓桦. 从性质之争谈我国政府在民办教育中的责任[J〗 .文教料,2008(15):105-106.
[3] 胡天佑.我国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与治理[J].教育学术月刊,2013 (7):14.
《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教育培训机构的规定是教育培训机构在法律上的最基础的法理依据,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界定也应当在此范围内进行。从《民办教育促进法》来看,教育培训机构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模式,弥补了《教育法》规定的僵化性,符合我国当前的教育培训业发展的潮流。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章关于学校和组织和活动的规定来看,营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的组织及运行基本符合《公司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这就说明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界定可以参照《公司法》的关于法人的规定,结合教育活动的特点和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教育培训机构的相关规定。综上,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宜定义为“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以确定的培训内容为目的从事非义务教育活动的组织”。
在我国现行《合同法》的立法模式下,由于教育培训合同未被规定为有名合同,对于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规制较为匮乏,通过对教育培训机构法律地位的分析,在“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下,适用《公司法》关于商主体的法律规定较为合理。反观《教育法》抑或是《民办教育促进法》都仅仅是简单介绍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及基本的程序审批规定,并未对准入门槛、退出机制、经营范围、责任承担等问题做出详尽规定。在今后的立法活动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kk体育,释明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主体及法律适用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法律机制,使教育培训机构在完善的法律监管之下科学健康地发挥作用。
由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特征不难看出,教育培训机构符合商主体的法律特征和我国《公司法》关于商主体的规定。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民法典》,通说认为我国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法与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事主体制度并不能涵摄和解决商主体的所有问题kk体育,所以商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主体,需要法律进一步加以健全。作为商主体的教育培训机构,自然可以从事经营活动并获得收益,目前监管治理进行中的“一刀切”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再结合《民法总则》来看,《民法总则》将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kk体育,从国家社会治理的角度而言,将教育培训机构完全纳入商法人的范围,并结合《民法总则》将教育培训机构分为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也并无不可。由于教育培训机构的特殊性和准入条件的严格性,结合《民办教育促进法》的立法原意,均体现了不宜给予过于宽松的准入门槛的立法目的。综上所述,在将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界定为商主体之后,在法律监管体制的设计中应当考虑《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并结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教育培训机构的准入条件予以考量。
周江洪(2010)指出教育活动并不单单是教师教、学生接受的过程,而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无论是对于教师还是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在人格接触上互教互学。其观点直接展示了教育活动的特殊性,教育培训更是如此,教育培训机构不仅为受教育者提供符合教育活动的物质满足,而且提供了特定的教育培训内容。笔者认为,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教育活动不仅要完成教育培训的内容而且也应当符合教育活动的一般规律,而不应该局限于培训任务的完成,同时也应该最大限度地兼顾教育机构与受教育者的人格接触。这就要求教育培训机构在设立时应当经过法定审批,保障其教育活动符合一般教育规律。
胡东成、彭瑞霞(2011)将教育培训机构的标准确定为遵循政府关于教育培训办学的规范、有助于帮助政府推行教育事业和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等要素。胡天佑(2013)在《我国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与治理》一文中将教育培训机构定义为国家教育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从事非学历教育培训的机构。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笔者认为现如今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并未有明确定论,学者的研究也多基于国家政策因素或者从教育管理角度进行界定。教育培训机构的监管始终要围绕法律的规定,如何对教育培训机构的概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明确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律地位就十分必要。